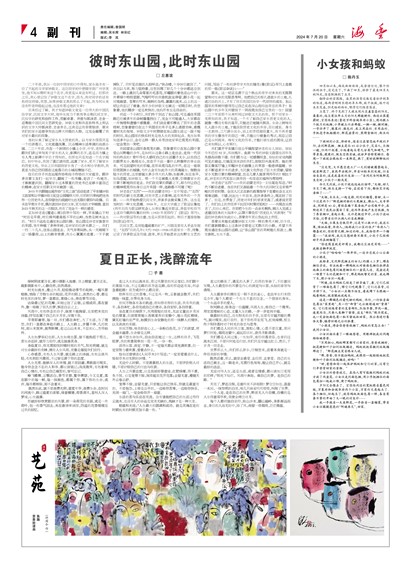□ 丘惠谊
二十年前,我从一位初中同学的口中得知,家乡海丰有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钟敬文。这位同学初中便辍学到广州学美发,他不知从哪听来这个名字,我更是从来没有听过。但那次之后,我心里记住了钟敬文这个名字,因为,我对同学的话有些将信将疑,我想,如果钟敬文真的那么了不起,我为何从来没有听老师提起过他,也没有看过他的文章?
后来经过了解,我才知道钟敬文竟是一位伟大的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并曾与郭沫若、老舍一道筹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钟敬文竟和我在教科书上所认识的文学大师郭沫若、老舍齐名,这真是让我非常惊讶。原来我们的家乡还曾孕育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家乡最初的印象。
当初从未了解过家乡人文历史的我,以为家乡仅仅只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底蕴浅薄,民众精神生活单调的海滨小城。二三十年前,我在一个封闭的小镇上小学、中学,老师从未跟我们讲过半句关于家乡的人文,彭湃的名字,还是因为镇上有人考上彭湃中学后才得知的,但那也只是知道一个名字而已。初中毕业,我到了湛江读师范,远离了家乡,更不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我甚至为自己仍旧困在这座落后的小城而懊恼不已。
往后的日子我在汕尾作协和海丰作协的大家庭里,跟许多前辈文友们一起学习,翻阅了一些书籍,走访了一些地方,才渐渐意识到,翻阅家乡这本厚重的历史书已足够丰富自己的精神,在家乡任职又何来被困一说。
2015年我跟随汕尾作协“文化之旅”活动走进了平东镇钟敬文故居和公平镇钟敬文纪念公园缅怀大师。但那时只单纯把他当作一位历史伟人,在仰望他的成就时生出无限的景仰与敬佩。后来在平常日子里,偶尔读到钟老的文章,更为他的才华倾倒。直到2023年秋天的这一次探访,我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正如钟老在《履迹心痕》自序中写的一样,平东镇山下村“村前是平原,村后排列着高低不平的山岭,当然是树木丛生的。”村后不远处是通往东山园的路。东山园是钟老家族昔日的果园,当年种植了多种果树,是钟家的经济来源之一。我们一行二十几人,往东山园走去。天气非常闷热,头一天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山上的路非常滑,我小心翼翼的走着,一下子就掉队了。只听见前面的人招呼道:“快点喽,十分钟后就到了。”我信以为真,努力坚持着,没想到爬了好几个十分钟都还没到达。一路上遇到几朵零星的毛菍花,那耀眼的紫色在山中的一片翠绿中特别显眼,气喘吁吁的我借机驻足停留,跟小花一起对视凝望。苍翠的竹木,婉转的鸟鸣,潺潺的流水,山上的这一切让我忘记了疲惫,当年少的钟敬文也被这一切吸引时,我想象着,他的脚步一定是欢快的,他的汗水也是自由的。
将近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东山园,可是通往果园路已经被多年的杂树藤蔓挡住了,完全不可能通人,大家都在一片惋惜和遗憾中感慨着。我们谈论着那棵长了百年的老荔枝树,想象着曾经在这个果园里的果子是多么清甜美味,感慨着时光的匆匆。钟敬文少年时期曾在东山园生活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东山园里的快乐时光是他人生的美好起点。先生如果知道多年以后,会有这样一群人来寻访他家早已荒芜的果园,一定会莞尔一笑吧。
我回望东山园那条荒芜的路,想象着那位在东山园中享受山间野趣的少年,是如何从这条小路上走出去,走向一代宗师的终点的?常听得有人感叹自己的生活圈子太小,以致自己的眼界太小,格局太小,实在干不出一番什么样像样的事业出来。可是回望时光的那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这一座依旧贫困狭小的城镇,为什么会有如此伟大的灵魂诞生。细数海陆丰的历史,这里曾诞生多少伟大的人物:如彭湃,如丘东平,如马思聪,如钟敬文。哪一个不是被载入史册,引领着家乡的后辈不断地向前走去。我们在前辈的荫蔽之下,却为何让自己的精神荒芜得如身后这片果园一样,连路都不可循了呢?
钟老在《“五四”——我的启蒙老师》一文中写道:“‘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化思潮,对我学艺上的影响,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我开始热爱民间文学,并亲手去做采集工作。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思潮。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两年后改为歌谣研究会),从事征集近世歌谣,并在学校日刊上逐日刊载所收集的材料(1923年更印行了《歌谣》周刊)。……我对歌谣等的注意,也是从那里引起的。稍后才直接接触到《歌谣》周刊。
民间文艺,是到处蕴藏着的矿产。问题是要有人手去发掘它。“五四”后的几年(大约1922—1926)我在家乡一带,搜集、记录了许多歌谣及传说、故事,并且开始思索这些野生文艺的问题,写出了一些初步带学术性的随笔(像《歌谣》周刊上连载的那一组《歌谣杂谈》)……”
原来,这一切正是源于这个热血的青年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和对生命的无限思考啊。他把自己的根扎进故乡的土地,扎进民俗的沃土,才有了日后我国民俗学一代宗师的成长。东山园里的果树何曾埋怨过自己长在深山而结出青涩的果子?东山园中的少年又何曾囿于一隅而荒废自己宝贵的一生?回望二三十年前那个从未听闻过钟敬文大名的我,那个对家乡一无所知的我,我才知道,一个不了解自己家乡历史文化的人,就像一棵没有根的蓬草,只能迷茫地随风飘荡。生命之树唯有扎入故乡的土地,才能汲取历史文化的养分,茁壮成长。身为一名教师,三尺讲台虽小,肩上的责任却很重大,我不再希望我的学生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只能应付疲惫的考试,而忘记自己是从何而来。唯有文化的传承,才能打破生活的困境,让自己来知所以,心有所归。
我们离开平东镇后往公平镇探望钟老的女儿琼姑。琼姑今年已经92岁,风烛残年。鱼街75号的钟敬文故居也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我们都为这一切感慨叹息。琼姑的家境肉眼可见的窘迫,但她见到来访的我们,却依旧兴高采烈。她的笑容正像客厅墙上那幅钟老的画像上的笑容一般慈祥温暖。钟老不断追求学术的进步,为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留给家乡无数后辈的精神财富,岂是几辈人能享用得尽的!相比于此,钟老的后代实在应该得到一些实在的福利与帮助呀。
钟老在《“五四”——我的启蒙老师》一文结尾处写道:“时代不断前进着。当前我们又面临着一个伟大的同时又是非常严峻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正在新的政策指导下走着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不错,比起七十年前来,在许多条件上,现在好了很多了。但是,世界变了,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或者说更苛了。我们肩上的责任并不比任何时期更轻松!……我现在虽然老了,但壮心未已。我要把今生的一点余光剩热,倾注入完成上述建国任务的大海洋中,以期不辜负那‘历史巨人’的教导!”年迈的钟老尚有如此壮心,吾辈青年更应负起肩上责任。
吾辈虽未能长成像钟敬文大师一样的参天大树,但今日,我们重新踏着山上这条钟老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希望不再荒废通往东山园的道路,让“东山园”里的果树能扎根故土,焕发新机,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