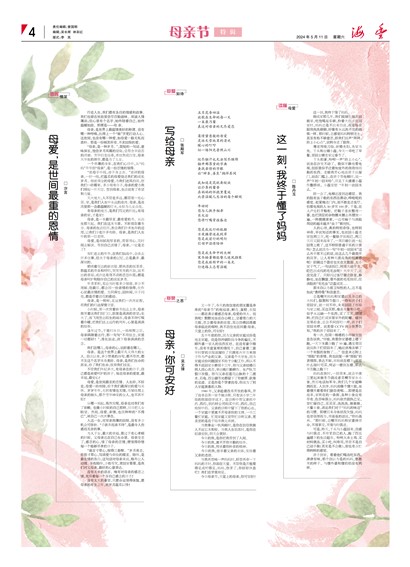□ 陈丹玉
这一刻,我终于懂了妈妈。
刚成家那几年,我们姐妹仨每次回娘家,吃饱喝足乐够,拎着大包小包回家时,妈妈总是不出来目送,而是躲在厨房洗洗刷刷,好像有永远洗不完的碗筷一样。那时候,总感觉妈妈特别老土,甚至有些不够意思,跟我们说声“拜拜,路上小心点”,就转身进了厨房。
尊重传统习俗,新婚夫妇,夫家为先。丫头和女婿小温,今天一早吃了早餐,要回女婿老家过春节了。
丫头的爹,吩咐一声“路上小心”,就坐在沙发不动了,貌似平静地看电视,但眼里似乎泛着如室外的微微细雨般的东西。老娘我开心地送孩子出屋门,站在门槛上,在孩子等电梯时,说一声“年初一回来哈”,只见丫头搂着小温作撒娇状,小温安慰“年初一就回来么。”
好一会了,电梯还没到达楼层。我的脸有虫子般的东西在滑动,哗啦啦的感觉。赶紧缩进门内,却不敢走进客厅,怕看电视的人50步笑100步。于是,在入户处打开鞋柜,把鞋子重新整理一番,也把顶层的杂物挪来挪去再摆放一遍,一阵摸摸索索,一边用袖子与满脸爬动的越来越多“虫子”做对抗。
人的心理,真的特别奇怪,也特别神奇,早就知道的事实,也就回小温老家住两三天,吃一餐除夕饭而已,两三天后又回来海丰了,一周后娘仨就一起回莞上班了,这不特别普通平实的日常吗?怎么就因为一句“年初一就回来”这么再平常不过的话,就这么几个最简单的汉字,让人有种天涯海角的别离感呢?眼睛这个器官也实在太脆弱、太小家子气了,一句话而已,何须大动干戈,眨巴出成线的毛毛虫呢?大半天了,还没完没了。只好闪过客厅溜进卧室,静静地,坐在飘窗,看外面的毛毛细雨,任满脸的“毛毛虫”泛滥成灾......
原来自以为前卫知性的人,还不是如此“奥特曼”和没意思。
总是嘲笑妈妈和家婆以及身边的大妈们,假期和节假日,一得知孩子们要回家,就一刻不停,来来回回于市场与家之间,买这买那,准备大餐和小吃,似乎永远缺一个东西,买了又买,团团转,把自己忙成家里家外的陀螺。碰到左邻右舍,总会不问自叨一声,孩子们要回来啰,就差借CCTV向全世界告知,“我的孩子要回来了。”
有一次,住同一栋楼的小师妹发信息告诉我,“师姐,我看你家婆楼上楼下跑,一天下来最少跑了10遍,遇见邻居就说孙子们要回来了,她应该准备够了一个寒假的食物了......”信息末还附上“捂脸”的表情。我也回复一串“捂脸”的表情图,表达不解,市场就在楼下,需要什么随时可买,何必一楼到五楼,那么辛苦跑上跑下?
妈妈在世时,一到周末,就会半夜三更起床做冬节鸽或者菜粿等家乡小食,然后电话如军令,我们几个家庭蜂拥而至。人到齐,妈妈却像个傻大姐,坐着傻笑着看我们狼吞虎咽......即便是在海丰,家所在的一条街,各种小食应有尽有,色香味俱全,妈妈依然固执己见,要忙碌自己,买买买,洗洗洗,做做做,大餐小食,满足我们对于“妈妈的味道”的习惯。即便后来身体状况欠佳,妈妈也要强撑而为,用爸爸的话说,“你妈高兴。”那时候,总嘲笑妈妈和家婆操劳命,不懂享受,不懂与时俱进。
可是,昨天,丫头与小温回来,自感与时俱进、不劳累自己的人,跑了四五遍楼下的生活超市,吩咐人杀土鸡、买材料煲汤,买小吃,叫寿司,尽管不是自己动手做(其实是不会做),却也有点忙得转转的感觉。
孩子到家,看着他们喝汤吃东西,津津有味,那个自以为是的妈妈,憨憨笑的样子,与傻外婆和傻奶奶没有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