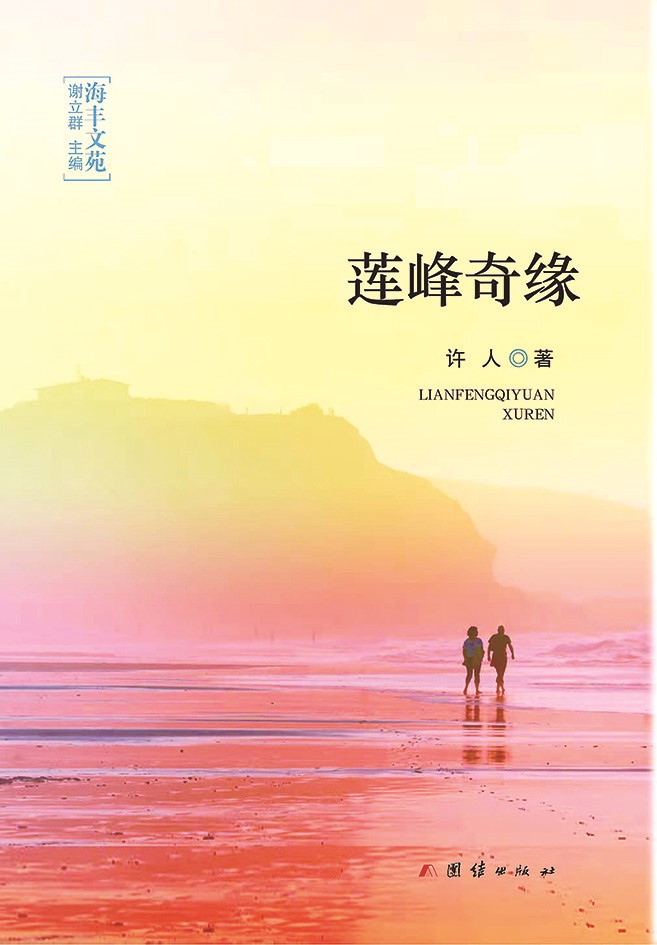
莲峰奇缘 许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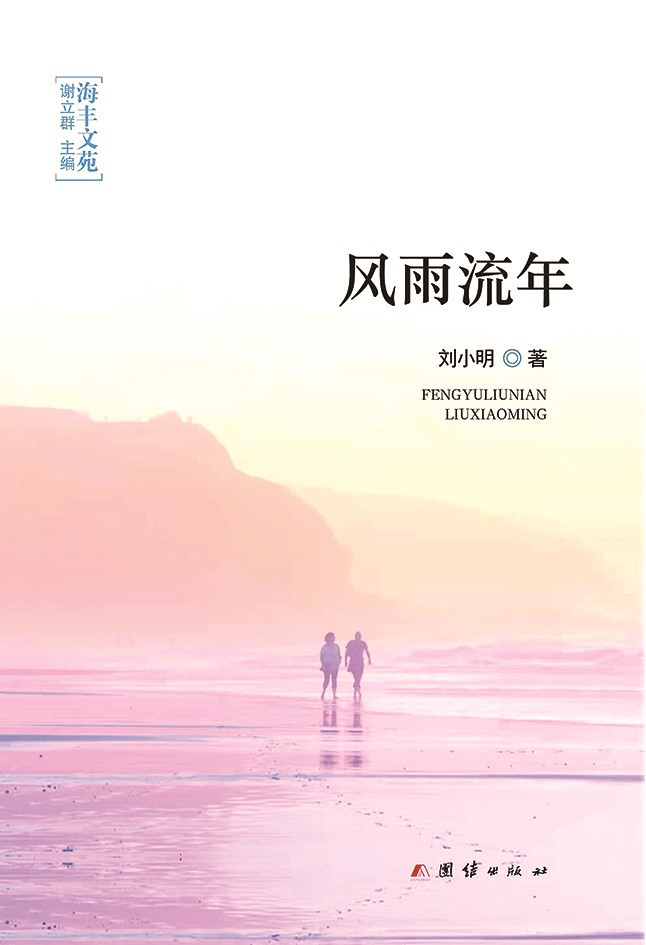
风雨流年 刘小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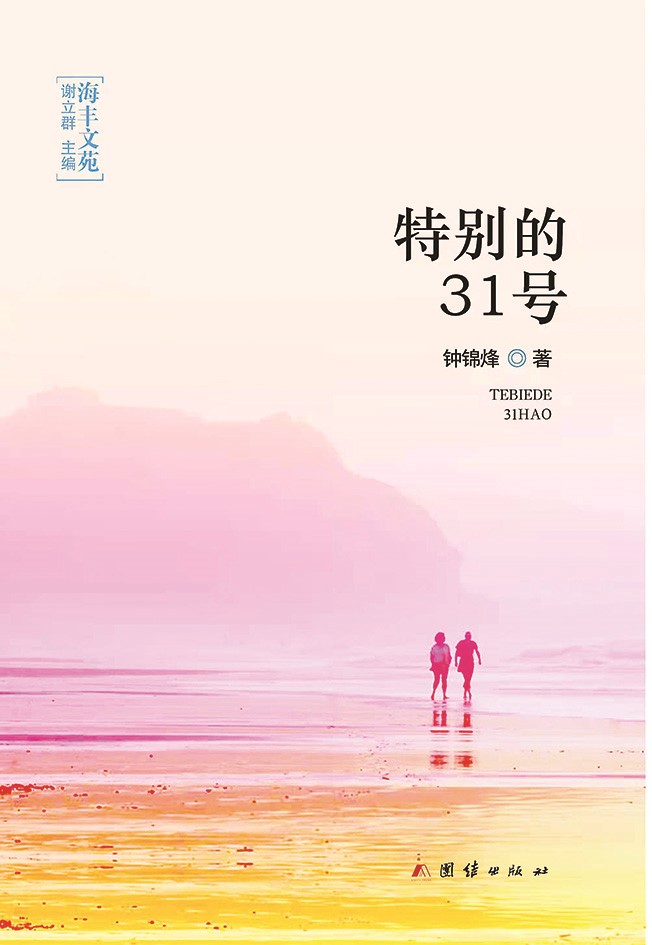
特别的31号 钟锦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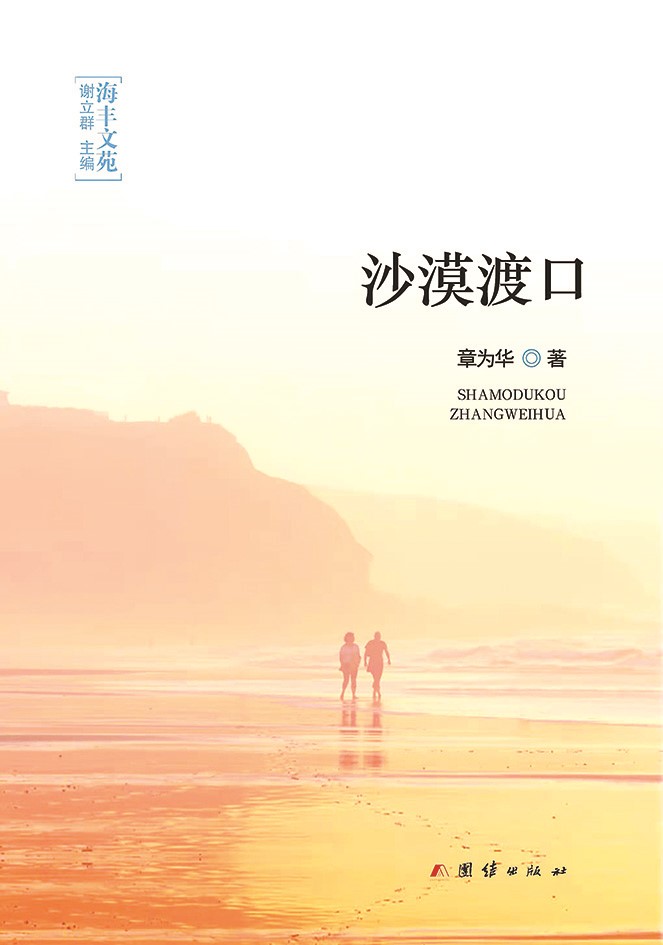
沙漠渡口 章为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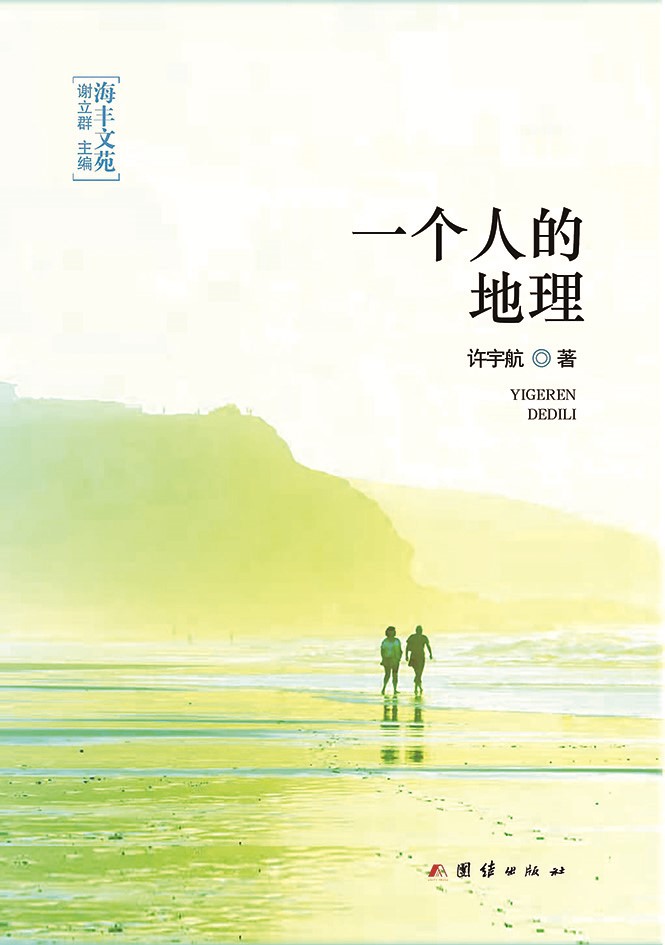
一个人的地理 许宇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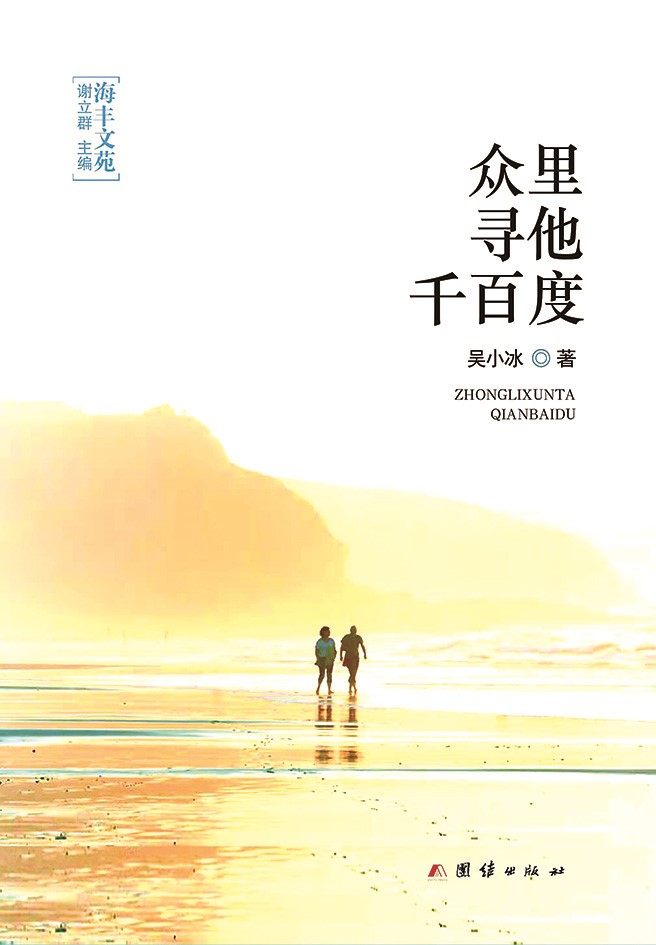
众里寻他千百度 吴小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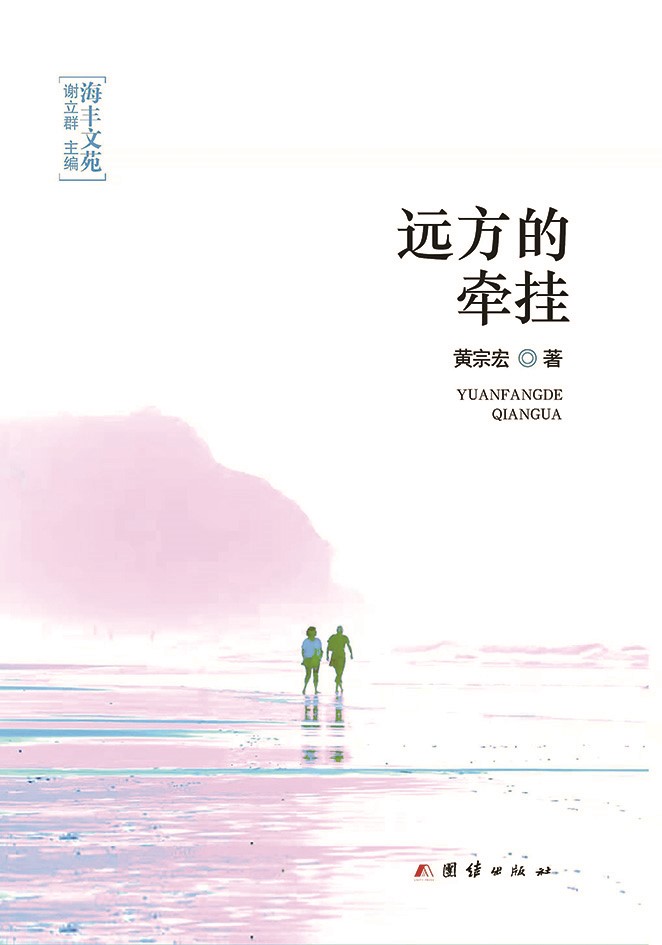
远方的牵挂 黄宗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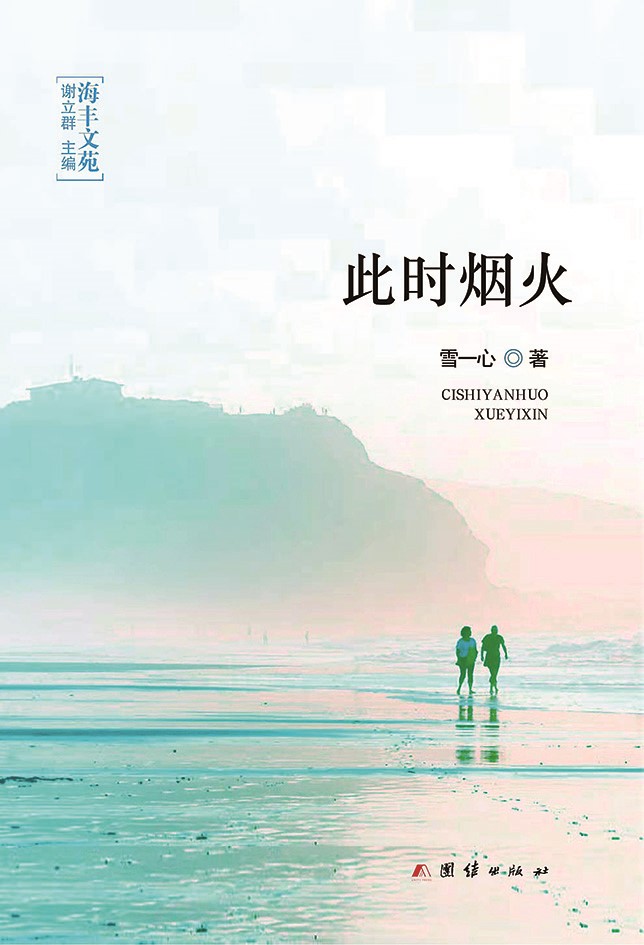
此时烟火 雪一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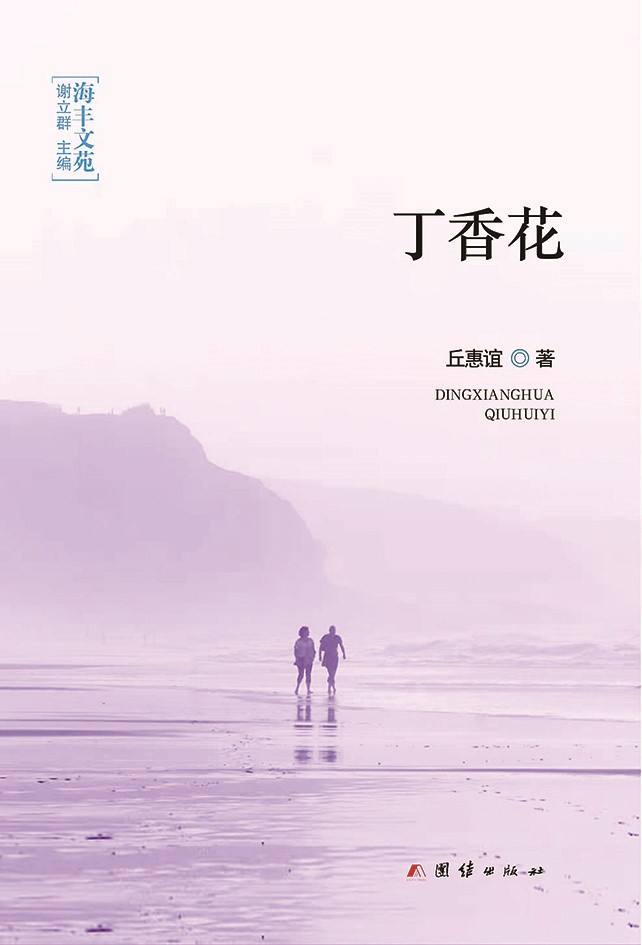
丁香花 丘惠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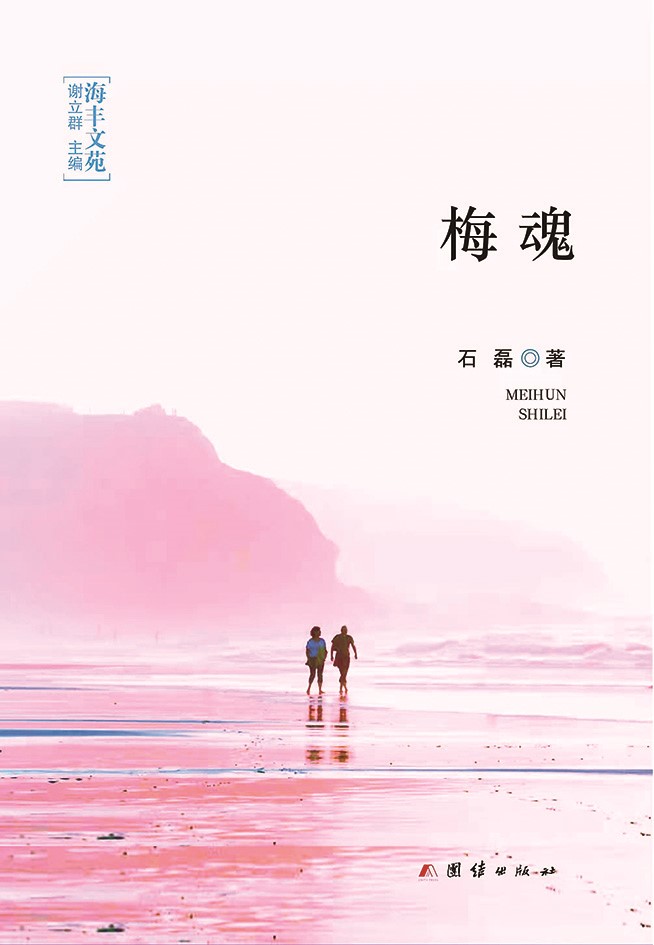
梅魂 石磊 著
《海丰文苑》序
● 谢立群
丘东平(1910-1941)是新四军著名烈士、我国军事文学的重要开创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一席之地。
2020年是丘东平诞辰110周年。为多方式纪念这位杰出乡贤,经和宇航、石磊等多次讨论,多次到梅陇马福兰村探访、座谈,初拟了一份丘东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工作方案,包括10项内容,其中有出版一套本地作家作品丛书的工作安排。方案草稿报有关县领导同意后,就着手准备纪念活动工作,这套丛书即由县作协负责征集、遴选。说干就干,一个月后,10本书稿基本上编好到手,于是石磊联系出版社,随后在2020年元旦前签订出版合同,计划5月纪念活动开展时跟读者见面。没想到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下子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了,一切聚集性活动取消,纪念工作方案没有印发,前期活动准备工作停止,这套丛书的经费顿时没有了着落。兜兜转转间,这套书在出版社躺了一年多,亏得县有关部门领导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如今即将出版发行,令人不胜唏嘘。
海丰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名人众多,民国时期就已经是岭南文学重镇之一,涌现出钟敬文、丘东平等名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华章。历经百年沧桑,进入新时代,海丰文学艺术活动繁花似锦,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走进实践深处,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创作出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巨变的文艺精品,以告慰先辈,启迪后人。
拉杂感言,权当作序。
辛丑年孟冬于海城
一个人的地理(后记)
● 许宇航
从第一本文集《十年前后》至今,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十年有多,这些年,好像时不时的在出走,利用一切可以出走的机会,全国各个省(区、市)除台湾、宁夏外都有所涉足。而这几年的工作,出外也成了常态,每年有几个月要在外住旅馆,行李还有异乡的床榻,成了几年来固定的元素,旅行所带来的陌生感,渐行渐远,旅行成了日常,对于游记写作来说,无异是一个杀手,沉淀下来的,也许只有疲倦。写作断断续续,原有清晰的文学梦想与计划,被生活、工作的琐事,消磨几近殆尽,如旧影片般布满遍体的划痕。唯一能坚持下来的只有写日记,如人生的速写本,做不到素描的精细,却试图用寥寥几笔把每天勾勒下来,这有时就为后来的写作提供了线索和可能。
如果说,之前的小集,以时间的名义结集,这一次,我借用了空间,在日记中抽出一些旅行的切片,以地理散文的名义再一次进行集结,尽管依然是那么的单薄。限于时间,或者从前的感觉已经消散这些借口,实际是懒惰和拖延的耽误,这本书中记述的是有关西藏、新疆、内蒙古、重庆、成都、铜仁、深圳、澳门、漳州、赣州、武夷山、潮州、三亚、海丰、陆河这些从前的边疆边地,其中一些篇章,还是逼宫之作,远远不及之前的写作规划,这就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约于八、九年前,我曾在《汕尾日报》的《教育周刊》写过一个专栏《行走者》,当时盛行行走文字,这本书中收入的约有一半的文字,也是彼时的遗产,编辑知我拖延,每周一篇,令我在催稿中前行,其时的宏愿是写完计划清单中的文字,出一本书,名字已经想好,就叫《出走者》。可惜事与愿违,不久报纸改版,加上工作变动,不复之前闲情,写作中断,一搁数年也就不了了之。走过的路,更多的只能继续在日记中沉睡,成了一片他人的留白。
我关注边疆边地已许久,边意味着远,我心目中的“边”,至少是旧时州府一级的交界处或者边城,远离中原,地处国角海边,这如同地质板块的碰撞之处,不同地域文化就在这样的地方触碰、撞击、交流、交汇、交融。因为远,一些东西消逝缓慢,得以在时间猎杀之前储存下来,落后有时成了旧文化的储藏之地,延续着文化的生命,这样的地方,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一县之内,边远有时可以是一处破旧的古村落,一座遗弃的旧县城,旧,其实是每个人心中的感觉,就在一念之间。这本书中笔触所至的边城边地,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的地理坐标,也是我内心深处的归隐之地。
文学于我,更多的属于精神的驿站,在我行走世间的行囊中,占据着一角,或许随着年月累积,对海陆丰地方史、民俗的关注和研究,所占的比重会大一些,但不可或缺,构成了我业余的两条主线,互相交织、缠绕前行。文学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以《一个人的地理》命名,更多的是以这样的名堂,营造一份文学的孤独感,或者是为了招牌般的煽情。文友加兄长石磊、柳成荫、谢立群一如既往的提携,不觉已过二十年,来自文学高于文学的情义,因了年份而弥足珍贵,时间漂走了一些人一些事,但总有那么几个人,不离不弃,沉淀了下来。
多年来,妻子陆漫红包揽了家务,承担教育孩子的任务,负重前行,让我得以轻身工作、旅行、研究、写作,这份分担、分忧的扶持,又怎能说是文学之外?文学赋予的,更多的是文字之外。
出走相随相伴的就是归来,这如阴与阳,如影相随,如倦鸟还巢,或许我下来的文学关注,就是脚下这片属于海陆丰的土地。乡村往事、乡土风物、方言俗语、民间歌谣、稀有戏曲,这些往昔的寻常,正在消逝或已然消逝,隔了时间只能遥遥回望,只能假手文学,感伤而温暖的打捞,哪怕留住的只是过去的片言只语。当然,这样的一段话已经离题,变成了下一本书的广告词,有着空头的嫌疑,充满着理想的诱导,为着空悠悠的一个也许,开始着下一个的计划。
2021年11月16日
感恩生命中有你
——《特别的31号》后记
● 钟锦烽
“以后,我要写一本书送给你!”这是学生时代对一位同学应下的承诺。不曾想到的是,这承诺一应就是十几年,十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这位同学是否还记得这本书,但我却是一直不能忘怀的,答应过别人的事,怎能忘却?
时光荏苒,恍恍惚惚间就过了十几年光景。直至有一天蓦然回首,竟然发现岁月的光影里不曾留下一丝丝痕迹,哪怕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文字,于是心中不免一阵惆怅,想着这文字梦也许就只能是一个梦罢了。时间来到2016年3月,一天正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同办公室的同事突然说,你既然喜欢写小说,干嘛不试着投稿?我一愣,投稿?一股热烈的写作冲动腾地一下就旺盛了起来,当天就写了几篇小小说投到了海丰报。其实,她不知道的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过散文,有些还得了奖。
过了几天,一个从海丰报社拨来的电话坚定了我重拾梦想的信心,打电话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海丰报副刊编辑石磊老师,他说很喜欢我那篇《回家过年》的小小说,并安排发表在海丰报副刊。说真的,当时除了激动,更多的是感动,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一个编辑给一个陌生的小辈打电话。当年6月,海丰报副刊整版刊登了我的小小说,这更加坚定了我文学创作的信心。我知道,这是石磊老师对我的一种鞭策。如果没有这一通电话,没有石磊老师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这本小说集,更没有一个可以给同学兑现承诺的我。同时,一定要说的是,这一路走来,得到了谢立群和许宇航两位兄长的鼎力支持,他们亦师亦友,不断激励着我前行,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黄羌客家传统习俗》《海丰客家山歌》《海陆丰革命歌谣评析》这另外三本书的诞生,更不会有一个在文学路上笃笃前行的我。还有其他文友,他们或鼓励或批评,让我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行。
感恩的话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语言,记在心上就行。现在来说说这本小册子,几十篇小说都是近两三年写成,分为小小说和短篇小说两个部分。从选稿到交稿,前前后后修改了好几次,增加了不少情节,然后发现自己竟然只会在文字里自顾自地说话,心里猛地一惊,这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于是就开始注重营造一些融洽的氛围,顺便搞点小动作,或者打扮打扮,尽量让另一个“我”丰满起来。
对于写小说来讲,丰满起来了是一件好事,但又是一件坏事。曾试着写玄幻,写了七万多字就停了下来,不是因为故事写不下去,而是因为写着写着,发现自己经常晚上做梦,梦见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人或事或物,这让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很糟糕,于是就停了,也就不再写那些光怪陆离的题材。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选择的几十篇小说,大都来源于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比如《特别的31号》,是有一次下乡,同车的兄长说本地有一个女人生了三个小孩,但在晚年却得不到子女赡养,这让我触动很大,于是就写了短篇;再比如《相亲》,当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办公室,也确实有这么一个未婚女生,而且是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那种,于是就突发奇想,何不让她去“相亲”捉坏蛋?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相亲》后来竟然还得了一等奖。这些小说虽然大部份都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但作为一个年龄不小的年轻写作者来说,仍存在不少瑕疵,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位大方之家斧正。
最后多说一句,妻子常说我左脑进右脑出,心里不装事,其实,她不知道的是,要是心里装太多的事,就容易乱,小说散文公文就会不分你我他,这可是要不得的,所以每写一篇文章,我都是从头开始,写过的就写过了,绝不再提。但是,心里该装的人还是要装,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嘴笨笔拙,只有心中时常默念:感恩生命中有你!
2021年11月于海城
回眸 守望
——《风雨流年》后 记
● 刘小明
初冬的夜晚,静寂而深邃。明月如霜,夜色如水。
月光是如此清冷。阵阵夜风从窗棂吹拂进来,桌上的一堆书稿随风翻卷、恣意舒展。此刻,窗外正是一派夜幕低垂、满眼星辰、璀璨无边的景象。
置身于俗世的尘埃之中,漫行于时光的长廊深处,天地悠悠而人生苦短,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岁月荏苒,流年似水。
向往缪斯女神的感召,由衷热爱文字,竟成为自己一种与生俱来的志趣,无论顺境抑或逆境,无论激昂还是沉沦,从未放弃书写、从未停止吟唱。
2010庚寅之年,少不竞时,有幸拾掇文章、集稿成书,名为《寻梦》,收录的大多是一些青涩的文字,仅是对生活的向往而已,寓意在人生朦胧懵懂之际,寻找心中的梦想、构筑坚实的希望,向着光明处奔腾、奋进。如今年过不惑重新执笔,竞已是十年之隔,一些零乱的书稿重新结集,名为《风雨流年》,文字不见长进、依然青涩,却多了一份对如烟岁月、似水流年的深切感悟!
人生在世,如沧海蜉蝣,如苍穹星宿。历经风雨的洗礼,历经生活的磨砺,历经流年的转逝,往往会有或多或少的文字凝于笔尖纸上,会有或深或浅的感悟藏于字里行间,尽管杂乱晦涩,也是自我的一种抒情释怀轻吟低唱。
《风雨流年》结集有些漫不经,议有些诚惶诚恐,唯恐辜负了有心翻阅浏览的读者们请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在下一个十年轮回之际,再敬献给读者更多更好的文字!
筱秋于得意居,2021辛丑冬夜
在文字里起舞
——《此时烟火》后记
● 雪一心
听到人们叫我作家,心里很忐忑,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个文字爱好者。对文字的爱好,让我从年幼至今对它饱含深情,给了内心那一城繁华恰到好处的居所。
小时候看图写话,写着写着就觉得,文字中让谁快乐谁就快乐,让谁胜利谁就胜利,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美好的事情。是文字让灵魂离开身体去旅行,它们放开彼此的桎梏。
一开始写作文和日记,也写书信给同学。日记一本又一本,写着无以名状的惆怅,忧伤,读初中写诗歌,随笔,那些文字是寒色残荷,是芦花深处的孤舟,没有清欢喜悦,后来才知道,从小开始,便是敏感脆弱的女子。心里种满浩大的庄稼,总在不停地拔节,化成笔下干戈四起的世界,那里正值芳菲节,花千树,星如雨。
那时也不管写得好坏,语言有时清丽,有时尖锐,有时张扬,有时低沉,直到有一天,文学社的学长把样报亲自送到班里来,一石激起千层浪,更笃定自己对文字的追随。青春年少喜欢渲染自己,特立独行,写下的东西,大抵是轻薄跋扈的,但少年无不好。
我感谢年少轻狂,让羞涩的自己尽情去飞翔,那些文字,轻盈又惊艳。
常常觉得自己是植物,以前喜欢野百合,山崖上兀自开放,但现在不是这样了,我更愿意是茶树,在云南,在武夷山,都可。曾经的嫩芽,终会老如山岳,可真好,那时便是一棵古茶树。在红尘生活中不动声色,但心里是石榴,硕大饱满,苍老天真。
一个喜欢文字的女子,活得安稳闲适,活得一团喜气,但内心需要保持兵荒马乱的清醒,内心养一只困兽,时而不安焦灼,时而凌厉清绝,时而妖娆艳丽,催生笔下文字万般千种,绵绵暗香。再看向晚的孤烟,是旅人的愁,亦是慰藉,独钓寒江的凄清是禅意美感,秋光老尽,故人千里又何如?把无处可去的心草耕耘成自己的王国。
人生无非鸡零狗碎的光阴,写字就是把生活彻底打碎重组,在内心苦苦交战,几次三番,能使江月白,又使江水深。就像厨房熬着浓汤,一个厨娘得心应手,清楚火候,恰如其分加姜,加葱,加蒜,巧妙搭配,烟火热闹。禅师铃木俊隆说:“当你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自我及强烈的欲望,经过修行训练,磨损和洗净自我,变得相当柔软,像是纯净的白色丝绸。”写字见证着人生的修行,从年少到中年,一步步蜕变,我找到那个离开身体去旅行的灵魂,表达着自己最真实的内核——淡然,安静。写过美意醺人的文字,也写过华丽耀眼的,但现在更喜欢静默朴素。
蒋勋说:“在某一个意义上,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没有读者的。”所写的是记忆中前世的种种,对今生的独白。这样的独白是私己的,独有的,它与你失散,与你周旋,但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这一路的颠沛流离,还是宁作我,使人对自己加倍的珍重和坚持。
每一次写都是一次开始,孤高疏离,绵密坚定,温暖明亮,低温游移……在现实中羞怯,但在文字中放肆张扬。福楼拜说“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 杜拉斯说:“如果不写作,我会屠杀全世界的。”这些话听着万里奔腾,一意孤行。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爱上文字,和真爱一个人那样,是戒不掉的瘾,爱到忘记自己,以命相许。
距上次出书已七年,这七年,在文字里泅泳、打磨,足够一生一世去反复咀嚼。我感谢文字,让我心有冷香,因为文字面貌慢慢变化,青春作别,但目光坚定,内心有清泉流过。
我对文字眷恋不已,它对我不离不弃。人生的每一个十年,它始终都在,与我情意相投,腹心相照。是它让我把人世间的繁杂简化到极致,在春秋日月里率真起舞,飞呀飞。




